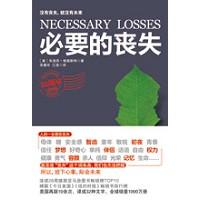品罢蜜露,再饮仙汁。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我们所有的丧失经历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那次丧失,即母子之间根本联系的丧失。因为在我们经历过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分离之前,我们和母亲一体生存。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我们与母亲亲密无间的状态;这是一种我就是你,你孕育我,你我同体的状态;这是一种和谐的交融状态;这是一种我浸于奶中而奶流淌在我身体里的漂浮状态;这是一种感受不到孤独与死亡的隔绝状态;这是爱人、圣贤、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和婴儿都熟悉的状态。人们称之为欢乐。
这种欢乐的最初联系是脐带联系,即子宫的生理一体。在子宫之外,我们也幻想那种同母亲化为一体的快乐。所以一些心理分析学家说,我们一生都渴望结合,而这种渴望来源于我们对回归的向往——如果不是回到子宫里,那便是回到一种虚幻的结合状态,即共生状态。这种状态“深深地掩埋在原始的无意识中,每一个人都为之而奋斗”。
我们并不记得自己曾待在那里或是离开那里。但那里确实是我们曾经拥有而又不得不放弃的地方。为了成长,我们必须放弃自己所爱,在每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都不得不玩这个残酷的游戏。这是我们最早的,可能也是最艰难的放弃。
丧失,离开,放弃乐土。
虽然我们不记得那片乐土,但永远不会忘记它。我们承认拥有天堂,也承认失去天堂;我们承认拥有一段和谐、完整的时光,享受着绝对的安全和无条件的爱,也承认那种完整已经被不可挽回地割裂了;我们承认它存在于宗教、神话、童话和我们有意无意的幻想中。我们既把它视为现实,也把它视为理想。我们全力保护那条区分你我的自我界限,我们也渴望重新拥有那片代表根本联系的失乐园。
***
我们总是希望重建一体关系,这种追求既可能是病态的,也可能是一种健康的行为;既可能是一种畏惧的避世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努力;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通过性、宗教、自然、艺术、药物、冥想,甚至通过外界刺激,我们试图模糊那条把我们分割在外的界线。我们试图逃脱分离的禁锢。有时,我们做到了。
有时,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例如性高潮,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一体状态。但是,在我们还没看清自己到了哪里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就像玛克辛?库明的优美诗作——《爱过之后》所描述的那样:
之后,便是和解。
身体又出现了分界。
比如这些腿,是我的。
你的胳膊,你抽回
缠绕的手指,火热的双唇,
各自寻着自己的主人。
一切如初,
除了曾经的那个时刻。
那只狼,贪婪的狼,
站在自我之外,
轻轻地躺下,睡着了。
有人认为,这样的经历——两性的肉体结合,把我们带回了婴儿时期的一体状态。当然,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巴克把性高潮称为“爱与死亡之间的完美调和”,它通过瞬间的自我消失来弥补母子的分离之痛。当然,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有意识地为了在床单之间找到母亲而爬上爱人的床。我们与母亲分离(这使有些人十分恐惧而不能达到性高潮)之后,性的交合给我们带来了欢乐。部分原因是,它在无意中重复了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次联系。
无疑,查特莱夫人给我们呈现了一幅自我分离、情欲亢进的极乐景象:“她的自我随着一浪一浪翻滚的波涛离开了身体,越走越远,越走越快,直到触及那个地方的时候,她知道她触到了,她消失了。”另一位妇女描述了类似的自我丧失的经历,她说:“高潮到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家。”
然而,性高潮并不是使自我消失,使那只不眠不休、贪婪的狼入睡的唯一方法,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使我们超越自我的边界。
例如,我经常坐在(或是漂浮在?)我的牙医的椅子上,朦朦胧胧地漂浮在雾气弥漫中,“感觉世界上所有对立的事物(我们就是因为这种对立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而感到困难和麻烦)都融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在牙科诊室中经历过同样雾气的人,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上面那些话引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但不管是值得尊敬还是不值得尊敬的人,都认为药物的力量可以把他们带入融为一体的状态。
对其他人来说,实现和谐一体的状态最好通过自然界,或者通过推倒人与自然之间的墙,允许某些人在某些时间“从分离的个体回到有意识的一体融合状态,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有些人,如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从来没有体会过与大地、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所以他们坚定地认为:“我是我,自然是自然。”但也有些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从欣赏自然,而且还从成为自然中找到了慰藉和欢乐。他们通过融入自然,使自己暂时成为“广阔世界和谐的一部分”。
有时,伟大的艺术在某些时刻也能消除观赏者与被观赏者之间的界线。这些时刻就是作家安妮?迪拉德所说的“纯粹时刻”,也是令人震惊的时刻。安妮说:“我将终生不会忘记自己张着嘴、木然地站在那幅独特的油画面前的时刻,河水翻腾而上,在我的喉咙处呜咽着,然后又退回油画,在水彩的背后消失了,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着敬畏之情飘入画了。”
有些特殊的宗教经历也会使我们回到一体状态。当然,宗教启示能够无可辩驳地穿透我们的灵魂,正如圣女特雷莎所说,当她的灵魂回到她的身体里时,她绝对相信她曾置身于上帝,而上帝也曾置身于她。
神秘的结合通过各种超自然的经历成为可能。神秘的结合结束了自我。无论这种结合发生在男女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人与艺术创作之间,还是人与上帝之间,它都在转瞬即逝的一刻重复或是恢复了母子一体的强烈情感。在那种情感的笼罩中,“我,我们,你,都不复存在了,因为一体状态下没有任何区分。”
***
但是,我们仍要在精神病患者与圣人之间,在极端的宗教狂徒和真正的教徒之间作一些区分。我们可能会质疑通过药物或酗酒而产生的宇宙结合的合法性。一群宗教狂徒,有穿戴整齐的,也有衣衫褴褛的,他们宣称:“融于大众之中使我欣喜若狂,我正品味着因丧失自我而产生的无上欢乐。”此时,我们会怀疑他们的行为是否正当。
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体不是疯狂、绝望和永久的,我们才会觉得它是美好的。暂时消逝在油画中,对我们来说是美好的,但永远消逝在狂热的崇拜中就不美好了。同样,我们可能会觉得圣女特雷莎的神圣体验是可以接受的,而吸毒者对上帝那种飘飘欲仙的理解就是不可接受的。同时,我们可能还想把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性生活与共生的性关系区分开来,与可怕的逃避分离的性联系加以区别。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阴道性高潮曾经被认为是女人性成熟的标志。当一个精神严重失常的女人,陷入同母亲而非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幻想中时,她可能会体会到那种高潮。男人也同样通过性关系寻找妈妈:一名男患者报告说,每当他发现自己“思维狂乱”时,他就通过花钱找一个妓女来使自己摆脱“疯狂”。他俩赤身裸体地躺着抱在一起,直到他感到自己“融入了她的身体”。
很明显,融合有时不过是共生现象——绝望地回到无助的、依赖于人的幼年时期。当然,如果我们总是让自己的思维停留(固定)在共生阶段或者返回到(倒退至)共生阶段,表明我们的情感是病态的。儿童共生性精神病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人们认为它和大多数成年人的精神分裂症一样,都是病人不能建立或保持分离的自我与他人的界线。其结果是:“我不是我,你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既是你也是我,你既是你也是我;我搞不清楚你是我,还是我是你。”
最疯狂的是,这种你我融合可能是狂野的、恐怖的、激烈的,充满的是仇恨而不是爱。那种感觉便是:“有她没她我都活不下去。”那种感觉是:“她令我窒息,但她的存在使我变得真实,使我活了下来。”在最疯狂的时刻,无论亲近还是分离都不可忍受,而且一体也不是极乐,而是一种强烈的需求。
我们正在研究一种严重的疾病——精神病,但是共生问题也会引起情感障碍,虽不像精神病那么严重。
以C夫人为例。她今年三十岁,但还是那么迷人,而且还有些孩子气。在二十岁以前,她每天晚上都和母亲睡在一起,后来嫁给了一个宽容但又有些女气的丈夫。C夫人的妈妈就住在她家楼下的公寓里,她的妈妈每天都来她家里做家务,为她安排生活。但C夫人不能搬家,因为她一搬离这个地方就会生病。C夫人得了共生性神经症。她与儿童共生性神经症患者不同,她成长的主要部分都很正常。但是在她生活的其他部分,她的行为很像共生体的一半,而且她在无意中也把自己看做了共生体的一半。她心底总有一种她意识不到的恐惧:如果这一对被拆散了,她和母亲都将无法生存。
从C夫人诞生之日起,C夫人和她的母亲就是共生关系,她们彼此依附,同忧同愁。难怪她离不开自己的母亲。但是,即使是最健康的母子结合也要在日后走上分离之路。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哈罗德?瑟尔斯所说:“我们反抗,并且不愿发展成独立个体的最大原因可能是,我们感觉到成为独立的个体,会把我们或者逐渐把我们和母亲分离,和那位曾经与我们同体的母亲分开。”
我们必须把放弃一体纳入我们生命的必要丧失之列。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重新赢回它的尝试。
是的,我们都有一体愿望。但是对一些不那么疯狂的人来说,这种愿望可能秘密地支配着他们的生活,贯穿于他们的所有重要关系之中,影响他们每一个重要决定。一位女士,想在两个都很有魅力的追求者中选一位做自己的丈夫。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外出用餐的那位追求者,用勺子舀出食物并像妈妈一样把食物送到她嘴里的时候,她做出了选择。那位先生只是潜移默化地给予了这位女士婴儿般的满足,便立刻赢得了她的芳心。他就是她的选择。
精神分析学家西德尼?史密斯说道,“对于那些与我们的行为形成反差的人来说,他们对一体的渴望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渴望打造成一个重要的、执著的、可以塑造生活的金色幻想。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它可能会被逐步并且极不情愿地揭示出来。”
史密斯的一个病人说:“我总是感觉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人会为我做任何事,会用神奇的魔法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并且我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一直守着这些想法生活着,我不知道,没有了这些想法我是否还能活下去。”
***
永远抱着对婴儿哺育期的金色幻想,会使人在精神上拒绝成长。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愿望,渴望一体时刻,渴望抹去自己与他人的区别,渴望重新拥有那种类似我们早期与母亲一体时的精神状态。这些愿望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变态。
一体的经历可以缓解随分离而来的孤独。
一体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先前的各种局限,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精神分析学家把建设性地返回成长的一些早期阶段称为“为了自我回归”。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活会借此得以充实和增强;他们认为,我们有时候可以通过后退一步来促进我们的成长。精神分析学家吉尔伯特?罗丝写道:“为再结合而结合是心理成熟的基本进程的一部分。”
在《寻求一体》这部饶有趣味的著作中,三位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体经历具有潜在的益处。他们提出了一项在实验室里得到了证实的假设——引发对共生的幻想,即一体的幻想,能够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和举止趋于正常,同时结合那些改变行为的技巧,可以改进学生的在校表现,缓解恐惧症患者的恐惧感,帮助吸烟者戒烟,酗酒者戒酒,节食者禁食!
那本书的作者写道,在受控实验中确实产生了上述效果。在实验中,他们只给实验对象呈现阈下(所谓阈下,就是指刺激量低于阈限值,通俗地说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字条,即手拿一张字条,在被试者还没意识到要看的时候就一闪而过。字条上写着:“妈妈和我是一体。”
这些实验者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相信这个实验一定会产生效果?
在C夫人、要人喂饭的女士和史密斯医生的病人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体愿望能延续到成年,而且还能激发行为。于是作者认为,如果对一体的渴望未被满足会造成精神病或其他混乱行为,那么通过幻想满足这种愿望(渴望得到照顾、保护,渴望完整和安全感)也许能产生很多有益效果。
上文提到的那项实验就是在通过幻想满足实验对象。是如何满足的呢?
就像我们醒来时已经忘记但又使我们一天都神清气爽或是垂头丧气的梦那样,有些幻想也会在我们意识之外发挥作用。作者说,“妈妈和我是一体”的阈下信息能够激发对一体的幻想。作者接着说道,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子外,这个信息都激发出了良好的感觉和有益的改变。不管这些良好的感觉和有益的变化能否持续下去,它们都证明了一体幻想的心理学价值。
例一,两组极为肥胖的妇女都参加了一项节食计划,而且两组成员都成功地减轻了体重。但是那组进行了阈下信息实验妇女的体重比没有接受此实验的那组减轻的多。
例二,给一组在居住中心进行治疗的病态少年进行阅读测试,并把他们的分数同上一年进行比较。整组成员的分数都有提高,但是接触了一体信息的成员所提高的分数是那些没有接触此信息成员的四倍。
例三,一项帮助烟民戒烟的计划结束一个月之后,检查多少人仍在戒烟。接触了“妈妈和我是一体”信息的那组成员,有67%的人仍在戒烟;而没有接触此信息的那组成员中,只有12.5%的人还在坚持。
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因此得出结论:“妈妈和我是一体”的阈下信息是未来的一种治疗手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也不会被用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体。在床上,在教堂里,在艺术博物馆中,在那些意料之外的界线模糊时刻,我们终生追求的一体愿望得到了满足。这些转瞬即逝的满足和融合的经历都是美好的,它们加深而非威胁了我们的自我感觉。
***
哈罗德·瑟尔斯写道:“因为失去了先前拥有的共生关系,所以没有人会成长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也没有人会变得完全‘成熟’。”但有时候,好像我们能够实现完全的独立。有时候,那只狼,那只贪婪的狼,站在自我之外,既不会放松警惕,也不会俯身睡去。有时是因为我们过于恐惧,不让它睡去。
当然,蕴含着消灭自我的结合能够消除焦虑。在爱或其他情感中放弃或抛弃自我,可能会使我们感觉自己是在丧失而非获得。我们怎么会如此被动,如此着迷,如此失控,如此……难道我们不会发疯吗?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找回自己?被这样的焦虑笼罩着,我们可能是在设置障碍而不是设立界线。只要有什么事物威胁到了我们那不可动摇的自主权,我们都会立刻逃之夭夭,而且我们也会躲避任何情感屈服的经历。
然而,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对根本联系的追求,即对重新获得母子一体的追求。我们都活在某种程度的无意识中,仿佛我们被变成了不完整的人。虽然,最初结合的破裂是一种必要的丧失,但是它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口,折磨整个人类命运的伤口”。通过我们做的梦和我们编造的故事,重新结合的幻象延续,延续,延续……并最终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促使时间变换的力量是一种无法宽慰的哀伤。这就是第一件事被看做一种驱逐而最后一件事被希望是一种恢复和回归的原因。所以,记忆曳着我们前行,预言也只是美好的回忆——这里将成为天堂,我们都会像孩子一样睡在母亲夏娃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