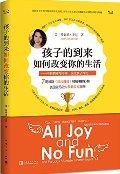第一章 关于自我管理
我将婴儿高高举到灯光下,充血的眼睛盯着一旁的医生,毫无感情地开口:“医生,您在这行已经很久了,所以请告诉我,”我重新将目光对准了手中的婴儿,“她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睡眠,毁了我的健康,我的工作,还有我和我妻子的关系……都是因为这个丑乎乎的小东西。”我艰难的吞咽着,终于问出了一直以来困扰我的简单问题:“我为什么喜欢她?”
——梅尔文·康纳,《纠结之翼》
在三月的一次明尼苏达州父母见面会上,我认识了杰西·汤普森。那个时节,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春意盎然 ;然而在明尼苏达州,孩子们还要等待一个月才能在花园里撒欢。我花了一个星期参加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亲子早教课程,倾听125名家长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一周里,几乎所有家长都会在某个时间点抛出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急需修复,就像家里孩子的玩具一样——橡皮泥硬得像石头,乐高积木丢得满屋子,完美再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每个听众都像久旱逢甘霖的旅行者,怀揣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爱,脸上写满了急需指引、卸下重担的渴求。
明尼苏达州的亲子早教项目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并成为该州独树一帜的特色项目,也是吸引我奔赴此地的缘由。只需一笔折价费用——有时甚至免费,任何三岁以下幼儿的父母都可以每周前来参加。父母们的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仅2010年就有近九万父母报名。
每堂课的主题都会变化,但都能给父母们提供吐露心声、交流学习和释放焦虑的机会。每堂课的前半部分都直切主题,父母和孩子在项目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进行互动。但课程的后半部分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父母将孩子留给专业教师看护,进入另一个房间,开始享受来之不易的45分钟“成人时间”,喝喝咖啡,放松装束,交换笔记,在一位教育家的引导下进行小组讨论。
我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小型课程上认识了杰西,几乎立刻就喜欢上她。她属于那种求知欲很强,对自身的美好却浑然不知的女性,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味道。她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虽然有时过于偏颇,比如“这都怪奥普拉”,也同时说明她不怕展露情绪的黑暗一面,甚至可以不带丝毫感情地剖析自己,像实验室的医生解剖小白鼠一样无情。比如课程中,她提到有次离开家去见友人,考虑到家里有三个学龄以下的孩子,简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有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或许有的母亲就是这样抛弃自己的孩子的。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她们为什么会跳进车里,一去不复返。”独处的狂喜蔓延到全身,她意识到开阔的道路中间只有她一人在疾驰,没有孩子在后座你推我搡,“有那么几分钟我真的开始认真思考,如果就这样一直开下去会怎么样?”
当然,杰西并不是真的打算实施这个疯狂的想法。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位负责的母亲,因而她能够在事后坦诚吐露这次逃离的假想。但更加确定的是,她已经精疲力竭,处于崩溃边缘了。她还梦想着将地下室扩展成为正式的摄影工作间,她的生活围绕着各种开销和花费,她最小的孩子只有八个月大。她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孩子的芭蕾或足球课程,更不用说学前教育这样的奢侈品,她甚至连每周一到两次早间保姆都请不起,每回去杂货店采购都要带齐三个孩子。“我偶尔也有自私发作的时候,”她说,“比如我不想再去换尿布,不想孩子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我。我只想跟朋友安安静静的通一次话,不被各种突发事件干扰。”
她极度怀念从前有额外收入的日子。但随着三个小孩子的到来,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就像三十年前艾玛·邦贝克书中角色的一针见血 :“自从十月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独自去过厕所。”
你一直是位意志坚定的模范,来去潇洒,不带走一片云彩 ;突然有天就套上了家长的角色,满负荷运转,从此告别正常生活的节奏。育儿初期的生活总被各种研究提名为最不快乐的体验,绝非偶然为之。在那段尴尬的时期里,新手家长缺乏育儿技巧,麻烦却总是不期而至,毫无停歇。曾经严格的自我管理变成这样一团混乱,亲子早教项目采访到的父母都抱怨连天。
一位选择在家陪伴两个孩子的父亲告诉他的家庭主“父”同仁们,有次他在街上遇到了即将赴古巴工作的前同事。“我当时就想,‘哇,简直太棒了’。”这位咬牙切齿的父亲用行动表明,这其实是他听到的再糟糕不过的消息了。他进而补充道 :“我见过看上去更自由的人,他们做着一切我希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可事实是我还有个家庭要照顾。实话说,我想不想要家庭?答案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我有没有在孩子身上找到慰藉?当然也有。但是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有时会蒙蔽你的双眼,直到有天你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在恰当的时候做想做的事。”直到最近,父母们的需求才得以浮出水面。只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欲望版图扩张过度,而我们所受的教育说,把愿望一一实现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权利(其实是义务)。历史学家罗伯茨在千禧年前的一篇论文中言之凿凿 :“20世纪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声鼓吹,人类的幸福是可以实现的。”真若如此,倒的确值得欢庆。但幸福并不算作切实的目标。如果现实达不到期望,我们常常归咎于自己。“我们的生活变成一曲挽歌,悼念不得不牺牲的愿望,狠下心拒绝的机遇,还有那些无从选择的道路”,英国心理分析家亚当·菲利普斯在《错过》中写道,该文收录于他2012年出版的散文集。“神秘的力量让我们相信,哀悼和抱怨是最脚踏实地的事情。”即使我们的梦想永远不能实现,即使它们从诞生之初就拥有巨大的缺陷,我们也会懊悔没能追随到底。菲利普斯说:“人们不能想象没有另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因而我们也不得不问自己 :如果一直就这样下去会怎么样?
如今,上天给了人们另一个自我欺骗的理由 :我们在孩子到来之前会拥有更多时间挖掘潜能。援引2010年国家人口出生率,一篇国家婚姻项目的报告显示,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已经达到30.3岁,并且此人群“倾向于选择婚后两年生育”。推迟生育进一步加深了时代的鸿沟,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对生活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记忆,用十年时间独居,尝试不同的工作、情感伴侣和生活方式。
在那一周亲子早教项目的课程中,几乎没人能像杰西那样坦诚地谈论育前和育后的变化。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曾远赴德国教授英语,在英国的酒吧打过工,还兼职做德尔塔航空的空姐 ;现在却成天困在一个300平米的屋子里,只有一个洗手间(不过房子条件还不错)。快要奔三的时候,她决定在广告业打拼出一片天地。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的事业的确走上了正轨 ;后来她开展了一种新的、更宜居家(她自己这样想)的生意,市中心安静的办公室变成了电视机对面的嘈杂小屋。“我真的,真的还在努力挣扎,”她对小组成员如是说,“三十二岁之前,生活里还只有我和丈夫两人呢。”
养育孩子从上百成千个方面扩充了我们的生活,也在上百成千之处打乱了我们自我管理的节奏,从工作到休闲,直至每天日常活动。本书会着手剖析这些被重组的事物,并尝试解释这些变化的缘由。被偷走的睡眠早上八点拜访一户人家的好处在于——如果你可以跨过每个人都衣衫不整一头乱发的心理障碍——可以从父母的脸上读出昨晚和今早发生的故事。
亲子早教课程结束几个月后,我来到跟我只有一面之缘的杰西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她的丈夫是位土木工程师,一早已经奔赴工作岗位了。杰西在家,满脸疲惫,旁人可以猜测她要么起得过早,要么睡得太晚。结果二者都是答案。
“你来之前,我已经抑郁到极点了。”她一边坦白,一边关上身后的门。她穿了一件红紫相间的坦克背心,长发还湿着,随意绑成一条马尾。 5岁的贝拉和4岁的亚伯正欢快地跑过房间,完全没有留意到母亲的倦容;婴儿威廉正在楼上酣睡。她解释说:“威廉醒得太早,其他人也起得很早,威廉还吐在他的毛绒玩具上了。”几乎就在同时,亚伯尿了床,意味着床单又要换,他也需要冲个澡。然后威廉开始在餐桌上乱喷果汁,仿佛一支压缩式吸管。“这才是早上7点37分的光景,我只能说,即使对于混乱来说也太早了。”这就解释了她起早的原因。而晚睡又是另一番光景。一般晚上是杰西得以不受打扰地工作的宝贵时间,但她手头上的活儿今天下午就要截止。让她沮丧的还有一件事 :为了节省开支,全家人不久就要搬去郊区了。这次迁徙理论上能够减轻她的负担( “税能减半,房租也能减半” ),但她在新社区没有一个相识的朋友。在忧虑和工作的双重煎熬下,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才沉沉睡去。
杰西承认,有的时候因为过于疲倦只能给全家准备牛奶泡麦片的早餐,“我也认得几位完全没有睡眠困扰的母亲,”她说,“可我就是不知道她们如何做到的,因为我显然无计可施了。”
在所有新手父母的烦恼中,睡眠问题是最恶名昭著的一条。但是无论事前做多少心理铺垫,大多数准父母只有在第一个孩子降生后才能准确理解它的含义。或许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了解被剥夺睡眠是怎样的情形,只是持续睡眠不足和偶尔难眠之间差异巨大。大卫·丁格斯,美国最权威的睡眠专家,认为按照对睡眠时间损失的反应划分,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基本能够很好适应的人,有点调整困难的人,以及灾难性崩溃的人。问题在于,大多数准父母只有在面对孩子时才能弄清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我自己就属于第三种,只要两晚睡不好,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
丁格斯怀疑,不论你属于哪种类型,这种属性都不会轻易改变。睡眠缺失导致的情感问题让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小组展开分析,通过对909位德州女性的调查问卷发现,母亲们相比洗涤衣物更不愿跟孩子待在一起。睡眠时间不足六个小时的母亲们相比于拥有七小时以上睡眠的母亲们,不幸福的感觉又上升了一个层面。这个差别如此巨大,甚至超过了年薪9万美元和年薪3万美元的幸福感的差别。(在一些新闻报刊里,这项发现有时被描述为“一小时的额外睡眠时间价值6万美元的升薪”,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也足够贴切。 )
2004年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两个月以下新生儿父母的平均晚间睡眠时间是6.2个小时,对于10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这个数字也没有大的改善,保持着每晚6.8个小时。其他的研究结果则稍微令人振奋些 :神经学家霍利·蒙哥马利·道恩斯就此课题也做了不少深入研究,最新的发现是新生儿父母平均每夜睡眠时间与非父母人群均为7.2小时,但关键区别在于睡眠是否连续。
无论从哪类睡眠研究看,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可以达成共识 :新父母们的睡眠模式是片断的,不可预测的,质量极差,连重塑身体及大脑机能的基础功效都无法达到。正如我在简介里所说,仅仅一小段睡眠缺失也可以达到消耗过量酒精对身体功能的妨害。“所以你可以想象连续三个月每晚只睡4个小时会有怎样的后果,”迈克·博内特说道。他是俄亥俄州代顿市凯特灵医学中心的临床主任,也是一名睡眠研究员。“我们较倾向于将它跟一系列副作用对比,这样那样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但跟酒精的对比才是重点,因为社会公认醉酒驾驶是应该受到责罚的。”
博内特补充道,缩短的睡眠易于激发怒气,却不易容忍和自控。这对竭力保持镇定的父母们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实际上,心理学家对于缓慢消磨的自制力创造了专门的词汇,叫做“自我损耗”。 2011年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提尔内合著的关于意志力的书籍,提出了一条重要的论点 :自控并不是一口永无止境的泉眼。他们通过调查200个受访对象,得出了一个最有趣的结论,即“人们越花意志力在某件事情上,越有可能在下一起突发事件上爆发”。
对我来说,这个结论带来的问题是 :假设父母们花费大量精力抵抗睡意,而睡眠又是人类两大主要宿敌之一(另一个对手是进食),那么到底什么会让父母们屈服呢?我能想到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想要大吼的冲动。没有什么比冲着整间房里最弱的人大吼能让父母们心情更糟了,但我们却总被拉入这样的循环,无法脱身。杰西承认生气时大吼就是她现在的状态,而她本拥有令人艳羡的成熟又温和的性情。“我会先吼他们,然后因为这件事内疚——为什么自己不能多睡会儿养足精力呢?”